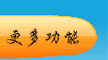我對斯蒂菲娜老姑總是懷著敬畏之情。說實在話,我們幾個孩子對她都怕得要死。她不和家人一塊生活,寧願住在她的
婚禮花車小屋子裡,而不願住在舒舒服服、熱熱鬧鬧的家裡--我們六個孩子都是在家裡帶大的--這更加重了我們對她的敬畏之情。
我們經常輪替著從我們住的大房子裡帶些母親為她做的可口的食品到她和一名黑人女僕一塊過活的那間小屋裡去。桑娜老姨總是為每一個上門來的怯生生的小使者打開房門,將他或她領進昏暗的客廳。那裡的百葉窗長年關閉著,以防熱氣和蒼蠅進去。我們總是在那裡哆哆嗦嗦、但又不是完全不高興地等著斯蒂菲娜老姑出來。
一個像她那樣身材纖細的女人居然能贏得我們如此尊敬。她總是身穿黑色衣服和帶
韓國手袋,與客廳裡的陰暗背景融成一體,將她的身材襯托得更加嬌小。但她一進門,我們就感到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充滿活力和剛強的氣氛,儘管她的步子慢悠、聲調甜柔。
她從不擁抱我們,但總是和我們寒暄,將我們熱乎乎的小手握在她那雙秀美清爽的手裡,她的手背上露出一些青筋,就像手上白嫩的皮膚細薄得遮不住它們似的。
桑娜阿姨每次都要端出幾碟粘乎乎的南非糖果和一缽葡萄或桃子給我們吃。斯蒂菲娜老姑總是一本正經他說些農場裡的事,偶爾也談些外邊世界發生
matchmaking的事。